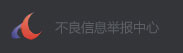-
资讯
- 时间:2021-12-27
“一部书画史,半部在湖州。”作为江南经济文化重镇,湖州自古繁华,文脉兴盛,不仅是“文房四宝”之首的湖笔产地,而且还孕育出诸多书画名家,如三国曹不兴、北宋燕文贵、元代赵孟頫、近代吴昌硕……皆可谓开宗立派之大师。此外,“二王”、智永、颜真卿、苏轼、米芾等书坛巨擘亦曾旅居菰城,或为官吴兴,其共同构成了湖州书画史上的璀璨群星。湖州之所以巨匠辈出、大师云集,在于其水路密布、交通便捷,故历来商贾云集、经济活跃、民众富庶。民国时期,湖州依然是水上交通要塞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,故引得众多钱庄、银行来此设立“分号”。时任中国银行湖州分行行长陈左夫,既是一位银行家,更是一位著名篆刻家。
更名“左夫”
陈左夫(1912-1998),名浩然,字左夫,以字行,江苏启东新港人,著名书法篆刻家,曾任中国银行湖州分行行长,生前系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,有《左夫刻印选集》行世。
陈左夫自幼聪慧,少时曾辗转就读于江苏海门启秀初级中学、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。1931年,他高中毕业,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,读经济金融。大学期间,爱好文艺的他选修了《文字学》,不曾想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。在老师指导下,他拿起刻刀开始刻印。由于是“左撇子”,用左手操刀,故字“左夫”,且此后以字名世。1934年,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中国银行工作,并因抗战爆发而随之辗转浙西工作。1945年,30出头的陈左夫因业务出色被调至中国银行湖州分行担任襄理,后任行长。湖州解放前夕,他还积极发挥自身影响,奔走协调,为湖州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放贷股股长;1954年后转至教育系统工作,先后在杭州第四中学和第六初级中学任教直至退休。

本文图片为陈左夫艺术作品
“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;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艺术之别材,首先在天分。但仅凭天分是难以大成的,后天之努力和所处之环境亦十分重要。若从这点来看,陈左夫无疑是幸运的。他大学毕业进入金融界,这在当时可谓衣食无忧。加之时值战乱,当局更加关注战局动向,而对文化艺术领域几无限制,使艺术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。战争还点燃了广大艺术家的爱国情怀,极大地激发了其创作热情与艺术灵感。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,陈左夫相继结识了邓散木、韩登安、余任天、谭建丞、林风眠、张宗祥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陆维钊等书法篆刻大师,交往颇深,耳濡目染。但难能可贵的是,他虽有诸多名家大师指点,但却没有轻易依附哪门哪派,而是一如既往地独自探索,正暗合浙派“思离群”之艺术精髓。
印外求印
创新既需天赋,也讲机缘。如果说石鼓造就了吴昌硕、吉金铸就了黄牧甫、封泥成就了赵古泥,那么上天也再次眷顾了陈左夫。1945年秋,他调到湖州中国银行工作。爱好藏书的人都知道,湖州是晚清闻名的陆心源氏“皕宋楼”“千瓦亭”藏书、藏砖所在地。当时,藏书早已遗失,而藏砖却完整地陈列在陆氏“千闲草堂”左右两侧的壁橱里。多达千余块汉魏六朝时期的墓砖除少部分为当时文人所书外,绝大部分出自工匠之手。这些天真烂漫的砖刻引起了陈左夫浓厚的兴趣,也打开了其“印外求印”的取法思维。
他的印章字法不落俗套,既有篆书的砖化,也有简化字的篆化,还有简牍的雅化,变化之丰富、组合之和谐令人叹服。章法则深受邓散木影响,以邓氏之“十四种章法”为基,继承其写意挥洒的“艺术灵魂”,并结合灵活多变之字法巧妙布裁,字随意变,意随字化,虚实互映,浑然天成。需要指出的是,其对邓氏之章法运用自如灵活,能根据入印文字之特点进行再改造、再创新,故印印不同、款款生动,绝无程式化倾向。其刀法亦独具一格,是少有的站着治印的印人,大刀阔斧,横冲直撞,犀利爽落,铿锵有力,极具视觉冲击力。由于站着刻印,常见20厘米见方的巨印作品,真率质朴、豪放粗犷、气势磅礴。为节省印泥,他还常用油墨拓印,足见其巨印之多。并且,其创新并非仅限于字法、章法和刀法,印屏亦颇有特色。


在某种程度上,其将印屏与印面等同视之,皆精心布局、巧妙化裁。比如,其印蜕与边款位置皆“不走寻常路”,似乱实整,似散实聚,给人以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感,使静态的印面具备了动态的节奏感;又如,其印屏的题签、长跋常用行草书就,瘦硬清癯,且与印蜕和边款参差交织、腾挪揖让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交相映衬;再如,其还善于将一首诗词以数印刻就,再制成印屏,其间加以长跋,使诗、词、书、印合成一璧,相映生辉,文气馥郁,新意迭出。因此,如果仅仅用“汉砖入印”来概括陈左夫篆刻艺术特征是远远不够的。在笔者看来,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能“遗貌取神”,不仅得取法对象之特质,更传承了“没有清规戒律可束缚”的工匠精神,远非寻常意义上的“印外求印”。
艺术推手
陈左夫之所以为当代印坛所重,除篆刻艺术成就外,还和他超强的组织活动能力有关,而这与其曾担任过商业银行分行行长是分不开的。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马一浮、马公愚、潘天寿、唐醉石、来楚生、韩登安、余任天等艺坛先辈相继离世。当时,篆刻艺术也处于“扫除”之列,篆刻界万马齐喑,有的印人甚至已无刀无石。但他以过人的胆识、对篆刻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执着,不顾年迈之躯,不仅为印人上门送刀送石,而且四处奔走,多方联络,冒着风险让自己的家成为当时印人的活动中心。这一时期,他与钟久安组织创作了《农民革命印谱》;1973年前后又与张根源等组织创作简化字印谱——《革命英雄印谱》,并积极与李伏雨等合作,借助“杭州书画社”这一平台多次推出小型篆刻作品展;1980年后,他又参与筹建杭州市书法家协会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、浙江篆刻研究会,协助举办“浙江省首届篆刻艺术展”“全国首届刻字艺术展”等活动,并将所藏12方两汉、三国、两晋砖砚及历代古砖拓400余页捐赠给湖州市博物馆收藏。
一直到后来西泠印社、浙江省文史馆、杭州政协书画会等机构举办的一系列篆刻活动里,皆有其忙碌操劳的身影。有事找“左老”,没事也找“左老”甚至成为浙江篆刻界的一种依赖……回首往事,浙江篆刻之所以能在全国印坛式微的背景下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,并在后来迅速复兴,成为国内印学中心,陈左夫功不可没。
“斜杠青年”
陈左夫才华过人,不仅篆刻、书法独步艺坛,而且在古文诗词、收藏鉴赏、学术研究领域也造诣深厚。如诗词方面,他曾作有《江城子·游芦茨》:“鸬鹚飞起钓台东,碧天空,去无终。山亭寂寞,高处乱岩中。惟有一江东流水,两岸绿,满帆风。”其词作格调清幽,不让古人。在鉴赏研究方面,其于青花瓷、玉器及汉砖等亦颇有心得,研究水准得到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、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的肯定,并与之合著论文,在《浙江历史年会》杂志上公开发表,至今仍备受推崇。为此,陆维钊曾专门撰联推誉:“操刀自成家,非骨甲樽彝,齐吴皖浙;鉴赏持新论,辩金铜玉石,砖瓦陶瓷。”

有人说,艺术家都是狂妄的。陈左夫亦不例外。他对自己的篆刻也曾自信满满地断言:“三百年后自有公论。”但应该看到,他不是一个“纯粹”的艺术家,其实还是一位严谨的银行家、浪漫的诗人、儒雅的学者、传道授业的教师、古道热肠的社会活动家……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讲,他是一位典型的“斜杠青年”。所以,很难说究竟是艺术成就了他的银行本职,还是银行本职成就了他的艺术,抑或是诗歌、学术成就了他的篆刻与金融本行……



 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编号:1101081994 版权所有:北京市一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C座1209室
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编号:1101081994 版权所有:北京市一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C座1209室